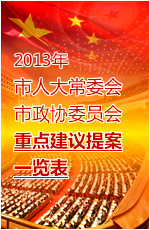案情:2011年6月16日,被告人庞全发在工商银行办理银行业务时,发现被害人王某的信用卡遗忘在自动柜员机里,在王某离开后,庞全发利用王某的信用卡在自动柜员机上取走现金5000元据为己有。
分歧:本案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:一是庞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;另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。
认为构成盗窃罪的理由是:失主将信用卡遗忘在ATM机上之后,使其信用卡中的款项处于极度风险之中,类似主人外出忘记锁门一样,此时窃贼入室盗窃,当然构成的是盗窃罪。
认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同志认为:一、拾得信用卡,破解密码之后,或者像本案直接利用遗忘在ATM机上的信用卡提出卡内现金,其行为特征表现为“骗取”ATM机的“信任”,而“自动”发出提款指令,应是诈骗类的犯罪;二、庞某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被“刑法”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为信用卡诈骗罪,且更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“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(ATM)上使用的,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规定的‘冒用他人信用卡’的情形”。因此有充足理由认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。
评析:笔者赞成构成盗窃罪。
理由之一:“骗取ATM机的信任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所谓诈骗是指利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,骗取他人信任,使他人做出不符合其内心真实意愿的行为。一,在多数情况下,诈骗的对象是自然人,在有的情况下,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会成为诈骗的对象,即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为诈骗的对象,但作出错误行为的人仍然是自然人,而将“机器”作为诈骗的对象,难以在情理上说的通;二,ATM机并未受到“欺骗”。庞某输入的各项指令均是正确的,因此ATM发出的提款指令完全是按照主人设计的程序,正确地履行自己的“职责”,不存在“受骗”问题。就目前的ATM机来说,还不具备识别用卡人和持卡人是否是同一人的功能,即使用卡人和持卡人非同一人,ATM机也无法识别;三,被欺骗者往往对自己的行为有“对”与“错”的选择,在选“对”的情形下就不会被骗,只有选“错”的时候才会出现被骗的问题。在输入的指令正确的情况下,ATM机只有一种选择,因此也不存在被“欺骗”的问题。
理由之二:从被害人主体的识别上,也足以说明,本案不是信用卡诈骗罪。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——本案的被害人是谁?则主张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同志很难回答,因为在本案中只能在银行和失主之间选择。如果选择银行,而在本案中银行并未失去丝毫的财产,因此不符合被害人的特征;如果选择失主,则失主并未也不可能受到行为的“欺骗”而作出错误“选择”。因此也不符合被害人的特征。有同志会认为,二者都是被害人,即通过“欺骗”ATM机的手段,而“骗取”失主的财产。如果有的同志持这种观点,则让我们先看一个类似的案例:在一个保管合同中,行为人持假的保管凭证冒充托管人,欺骗保管人将保管物提走。由于对托管人和保管凭证的识别都是自然人,保管人识别有误,而错误地将保管物交付给行为人,保管人是有过错的,因此造成托管人保管物的损失应由保管人赔偿,此案的被害人应是保管人。在本案中也是这样,如果认为银行是被骗对象,则理应认为银行作出了错误选择,由于银行存在过错,则应当赔偿失主因此造成的损失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如果认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,则银行应当赔偿失主的损失。我们不难看出,如果这样,则可能出现极大的道德风险。
理由之三:我们不能拿现实世界的眼光去看待虚拟世界。互联网、自动柜员机和自动售货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虚拟世界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虚拟世界都是现实世界的主体在操纵,但虚拟世界又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,在虚拟世界中,要遵守这些游戏规则。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,在互联网上购买一件衣服,该合同有效吗?这个问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。本案就存在一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交叉衔接的问题。对庞某在ATM机上发出指令提取款项的行为应用虚拟世界的规则去规范,对庞某拾取他人的信用卡(有的还有破解密码)的行为,和提取不属于自己的款项的行为用现实世界的规则(法律)去评价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在虚拟世界中庞某是遵守了游戏规则,在现实世界中,则违背了不得窃取他人财产的法律。
理由之四:司法解释未真正把握好立法者的立法本意。“刑法”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规定的“冒用他人信用卡”的情形,应当仅指冒用他人信用卡办理柜台业务的情形,因为办理柜台业务时要对持卡人的身份进行核对的,这才有“冒用”的可能,而且营业员如果怠于审查造成“冒用”成功,则银行是有过错的,应当赔偿持卡人的损失,此时的被害人不是持卡人,而是银行。
综上所述,本案的庞某乘王某不备窃取了王某处于风险之中的财产,应构成盗窃罪,而非信用卡诈骗罪。
|